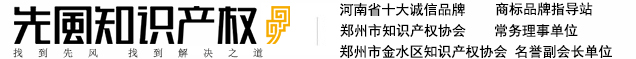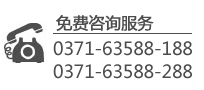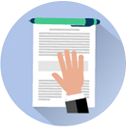縱覽全球大眾出版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出版業早已形成完整的產業經營鏈條,形成自己豐富多樣的經營模式,走在了全球大眾出版領域的前列,尤其是在版權經營方面。版權經營是出版最高境界,這是西方出版業的共識。
近年來,文學代理人也開始在國內出版界顯現,版權次代理機構方興未艾。國內大眾出版已經逐步向西方出版經營模式靠攏,與國際緊密接軌。
雖然國內的版權經營在認知層面逐漸深入人心,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但由于起步較晚,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卻仍有很多不足之處。針對“如何向版權要效益”這樣一個嶄新的命題,筆者認為傳統出版社應該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實際努力。
第一,是加大對獲取作者版權的重視力度。圖書出版歷來是傳統出版社的經典業務也是其強項。在這個過程中,出版社左手從作者或者其文學代理人手中得到無形的圖書出版權,經過編輯加工、復制,右手將圖書有形產品經發行商賣給讀者。而在其中,出版社對作者版權的獲取成功與否是關鍵。但從出版社近年來的實際狀況來看,出版社對作者版權的控制越來越弱化。從授權期限來看,這種控制的弱化主要表現在出版社圖書出版合同簽訂的時間越來越短,從原來的十年,到前幾年的五年,到現在的一兩年。而從授權性質來看,控制的弱化主要表現為非專有性質的授權在出版市場上呈現普遍態勢。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目前共有4個版本,就是非專有許可的明證。季羨林的《清華園日記》也是如此。這也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出版社對版權的控制越來越弱的觀點。
版權是一切版權經營的基礎,因此出版社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比如密切出版社與作者的關系,與作者進行充分溝通,構建長期利益共同體;在出版合同方面,借鑒西方出版社的做法,均衡風險,增強彼此間的信任,為長期合作奠定良好基礎等。從而加強對作者版權的控制力度,不斷豐富自身版權資源,夯實版權經營的基礎。
第二,是提升版權經營層次。國內方面,出版社要加強對附屬版權的關注和經營。對于附屬版權的重要性,交叉河流出版顧問公司總裁托馬斯·沃爾持這樣的觀點:附屬版權是機遇,同時也會是出版社主要的收益來源,是獨立的利潤中心。同時,他也認為附屬版權收益是增益性收益,出版社要自行評估它的利潤可行性。
附屬版權分為兩大類:一是出版形式附屬權,此項又可分為圖書形式(如平裝本版權等),期刊形式(如文摘版權等)和報紙形式(如第一連載權等)三種形式;二是非出版形式附屬權,如影視改編權及拍攝權、戲劇改編權等,近幾年來的影視IP熱也連帶著讓附屬權頗受關注。
對出版社來說,獲得附屬權的重要性除了獲得一定純利潤形式的收益,同樣還在于:其一,某些附屬權的使用與精裝書的銷售密切有關,二者可以合理搭配,盡可能地開拓圖書市場;其二,出版商可以與附屬權的使用者共同承擔版權使用費,以降低成本和減少經營風險。
在中外版權貿易方面,主要是加強版權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重點是自身運營能力。要想成功“引進來”即實現效益最大化,那出版社自身必須擁有強大的運營能力,能有效地對版權進行梯級開發,實現綜合效益;需要出版社把版權經營放到與資本經營的同等地位來管理和經營,將版權貿易作為出版社的主業之一來開展; 同時不斷加大對員工版權經營意識的培訓。在這方面,商務印書館無疑是為數不多的成功者之一。在第23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期間,商務印書館在“引進來”“走出去”上可謂碩果累累;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簽約,從劍橋大學出版社引進《劍橋希臘羅馬政治思想史》《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等8種圖書版權,輸出給劍橋大學出版社兩種圖書版權,還與牛津大學出版社聯合舉行新書發布會,推出《牛津中階英漢雙解詞典》;與新加坡名創教育集團舉行《全球華語大詞典》海外出版發行協議簽約儀式,授權其在東南亞地區以及英國、美國等地出版發行該書的中文簡體字版。
綜上所述,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版權經營中心轉移,傳統出版社必須適應市場,轉變以往經營模式,綜合開發版權資源。要想“向版權要效益”,傳統出版社必須在獲取版權和經營版權兩方面下大功夫,齊頭并進,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從而讓版權成為真正的效益來源。
本網站轉載的所有的文章、圖片、音頻視頻文件等資料的版權歸版權所有人所有,本網站采用的非原創文章及圖片等內容無法一一和版權者聯系,如果所選內容的文章作者及編輯認為其作品不宜上網供大家瀏覽,或不應無償使用,請及時留言通知我們,以迅速采取適當措施,如刪除或支付稿酬,避免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