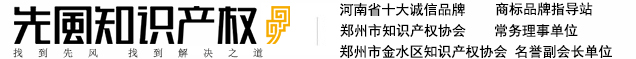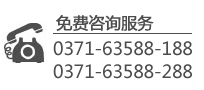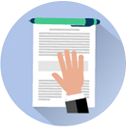【案情簡介】
美國旅安公司(Travel Sentry Inc.)是TSA(Travel Sentry Approved)行李箱安全系統(tǒng)標(biāo)準(zhǔn)的制定者且經(jīng)過了美國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正式認(rèn)可。“”是美國旅安公司最為著名的商標(biāo)之一并被廣泛使用在行李箱的安全鎖上,在市場(chǎng)上被稱為“紅鉆”商標(biāo)。2015年12月,美國旅安公司發(fā)現(xiàn)河北省保定市雄縣某公司、個(gè)體工商戶閆某所銷售的行李箱上使用了假冒的帶有“”商標(biāo)的安全鎖。隨后,美國旅安公司進(jìn)行了公證購買并向保定市中級(jí)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兩被告則辯稱自己銷售的商品是行李箱而非安全鎖,不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即使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在已提供商品合法來源證據(jù)的情形下,也不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
保定中院認(rèn)為由于兩被告所銷售的是帶有其它商標(biāo)的行李箱,安全鎖上的“”商標(biāo)不再具有識(shí)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因此判定美國旅安公司敗訴。美國旅安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到河北省高級(jí)人民法院。河北高院經(jīng)審理后認(rèn)為:安全鎖是行李箱的配件,雖然行李箱具有獨(dú)立的商標(biāo),但在安全鎖上單獨(dú)標(biāo)注美國旅安公司的注冊(cè)商標(biāo)仍然會(huì)引起相關(guān)消費(fèi)者對(duì)該部件來源的誤認(rèn)。兩被告提交的合法來源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其盡到了合理注意義務(wù)。最終,河北高院撤銷一審判決,改判兩被告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并承擔(dān)侵權(quán)賠償責(zé)任。
【案例分析】
在商標(biāo)侵權(quán)領(lǐng)域,最常見的情形是權(quán)利人基于注冊(cè)商標(biāo)權(quán)制止未經(jīng)授權(quán)生產(chǎn)、銷售注冊(cè)商標(biāo)所核定使用商品的侵權(quán)行為。但由于一些零部件產(chǎn)品通常接單生產(chǎn)且易于轉(zhuǎn)移,商標(biāo)權(quán)利人獲得侵權(quán)證據(jù)非常困難。美國旅安公司在打擊假冒安全鎖產(chǎn)品時(shí)即遇到了這一難題。相比之下,裝配有假冒安全鎖的行李箱在市場(chǎng)上卻隨處可見。因此,通過起訴行李箱銷售商制止假冒安全鎖在市場(chǎng)上的流通,成為美國旅安公司更加現(xiàn)實(shí)、有效的選擇。
本案涉及整體產(chǎn)品中假冒配件的侵權(quán)認(rèn)定問題。筆者代理了本案的二審程序,在辦案過程中進(jìn)行了大量法律檢索,發(fā)現(xiàn)類似司法案例寥寥無幾。地方工商機(jī)關(guān)曾在幾個(gè)行政查處案件中認(rèn)定產(chǎn)品中裝配的假冒配件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但沒有進(jìn)行較為深入的法律分析。先例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美國旅安公司一審未能成功維權(quán)的原因。
本案的兩個(gè)核心法律問題是整體產(chǎn)品中假冒配件的侵權(quán)認(rèn)定,以及銷售者的合法來源抗辯。結(jié)合辦案過程中的法律檢索及研究,筆者分析如下:
一、整體產(chǎn)品所裝配的假冒配件依然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但根據(jù)不同情形可能構(gòu)成配件侵權(quán)或整體產(chǎn)品侵權(quán)。
判定是否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應(yīng)當(dāng)首先認(rèn)定假冒配件上標(biāo)注的商標(biāo)是否屬于商標(biāo)性使用。未經(jīng)授權(quán)的非商標(biāo)性使用行為(描述性使用與指示性使用),不構(gòu)成商標(biāo)侵權(quán)。這一理論在我國商標(biāo)司法實(shí)踐中沒有爭(zhēng)議。
對(duì)于什么是商標(biāo)性使用,我國《商標(biāo)法》第四十八條做出了規(guī)定:本法所稱商標(biāo)的使用,是指將商標(biāo)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將商標(biāo)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yè)活動(dòng)中,用于識(shí)別商品來源的行為。該條款以列舉的方式對(duì)“商標(biāo)的使用”進(jìn)行了定義,并明確商標(biāo)使用行為的目的是“用于識(shí)別商品來源”。換句話說,具有識(shí)別商品來源作用的商業(yè)性使用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商標(biāo)性使用。
顯而易見的是,商標(biāo)必須結(jié)合商品使用(包括使用在商品宣傳或交易文書上)才能起到識(shí)別來源的作用。這就需要判斷整體產(chǎn)品中的“配件”是否屬于商品范疇。筆者認(rèn)為,配件和整體商品的關(guān)系和定位完全可以參照民法中的主物和從物。主物和從物在物理意義上應(yīng)當(dāng)是兩個(gè)具有可分性的獨(dú)立的物,需要結(jié)合在一起發(fā)揮作用。例如,羽毛球拍與羽毛球、電腦與CPU芯片、汽車與車輪等。如果一件物品相對(duì)于整體商品不再是獨(dú)立的物(如毛線與毛衣、化學(xué)品與油漆),則屬于原材料的范疇而非配件或從物。配件顯然具有獨(dú)立功能的,具有價(jià)值和使用價(jià)值,符合商品的基本屬性。
裝配有侵權(quán)配件的整體產(chǎn)品構(gòu)成配件侵權(quán)還是整體侵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基于相關(guān)公眾產(chǎn)生誤認(rèn)的具體情況來判定。也就是說,應(yīng)當(dāng)分析配件上的商標(biāo)所識(shí)別的是配件的來源還是整體產(chǎn)品的來源。比如,“INTEL”商標(biāo)識(shí)別的是CPU芯片的來源而非電腦的來源,“米其林”商標(biāo)識(shí)別的是輪胎的來源而非汽車的來源。通常存在以下三種不同情形:
1、侵權(quán)配件與整體商品可以輕易區(qū)分,且各部分擁有自身獨(dú)立的標(biāo)志,單個(gè)配件侵權(quán)不會(huì)使相關(guān)公眾對(duì)整體商品來源產(chǎn)生誤認(rèn),而是可能導(dǎo)致對(duì)配件所對(duì)應(yīng)的功能、質(zhì)量、來源產(chǎn)生誤認(rèn),如汽車與輪胎等,這種情形屬于配件構(gòu)成侵權(quán)。
2、僅能看到侵權(quán)配件,整體商品一般不帶有單獨(dú)的商標(biāo),容易使相關(guān)公眾對(duì)于整體產(chǎn)品的來源產(chǎn)生誤認(rèn),如電腦的機(jī)箱和顯示器、汽車的車體等,這種情形屬于整體商品侵權(quán)。
3、侵權(quán)配件被鑲嵌到其他配件中無法看到,不會(huì)使相關(guān)公眾對(duì)整體商品來源產(chǎn)生誤認(rèn),且相關(guān)公眾對(duì)于侵權(quán)配件也難以察覺,如計(jì)算機(jī)的CPU、汽車發(fā)動(dòng)機(jī)等。這種情形依然是配件構(gòu)成侵權(quán)。
本案屬于第一種情形,構(gòu)成配件侵權(quán)。誠然,大多數(shù)消費(fèi)者在選購行李箱時(shí)主要關(guān)注行李箱放置物品的功能,但許多消費(fèi)者也會(huì)關(guān)注安全鎖的品牌和功能。當(dāng)消費(fèi)者看到行李箱上帶有標(biāo)注美國旅安公司商標(biāo)的安全鎖時(shí),會(huì)誤以為安全鎖是由美國旅安公司生產(chǎn)或授權(quán)生產(chǎn)且符合TSA行李箱安全系統(tǒng)標(biāo)準(zhǔn)。一審法院的邏輯錯(cuò)誤在于否定了安全鎖獨(dú)立的商品屬性,并將整體商品即行李箱作為配件商標(biāo)的識(shí)別對(duì)象。同時(shí),通常來講侵權(quán)配件往往存在質(zhì)量隱患,組裝在產(chǎn)品上無法達(dá)到真品效果。如按照一審法院的邏輯,生產(chǎn)者、銷售者在將侵權(quán)配件安裝到整體商品之后既可“逃脫”侵權(quán)責(zé)任,顯然不符合《商標(biāo)法》的立法目的。
二、銷售者主張“合法來源”抗辯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舉證責(zé)任
我國《商標(biāo)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針對(duì)銷售商的侵權(quán)賠償責(zé)任規(guī)定了合法來源抗辯制度: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cè)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據(jù)此規(guī)定,銷售商要免除賠償責(zé)任,不僅要證明自己不知道所銷售商品是侵權(quán)商品的主觀狀態(tài),還應(yīng)舉證證明所銷售的侵權(quán)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
主觀狀態(tài)分為三種:明知、不知道但應(yīng)當(dāng)知道、不知道且不應(yīng)當(dāng)知道。由于商標(biāo)侵權(quán)采用過錯(cuò)推定原則,因此銷售商適用“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狀態(tài)只能是“不知道且不應(yīng)當(dāng)知道”,否則將不合理的增加權(quán)利人的維權(quán)難度。當(dāng)然,是否“不知道且不應(yīng)當(dāng)知道”與銷售商的認(rèn)知能力以及被侵權(quán)商標(biāo)的知名度程度密切相關(guān)。
舉證證明所售商品的合法取得是適用“合法來源”抗辯的另一必要條件。“合法取得”是指進(jìn)貨渠道的合法。在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銷售商在沒有主觀過錯(cuò)的前提下,以合理的價(jià)格購買商品,即使實(shí)際上侵犯了他人的注冊(cè)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但也應(yīng)視為合法取得。但是,根據(jù)“誰主張誰舉證”的樸素舉證責(zé)任分配制度,銷售商有義務(wù)提供購貨合同、付款憑證、發(fā)票等有效證據(jù)對(duì)合法取得予以證明。對(duì)該等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注重對(duì)證據(jù)的真實(shí)性、證明力、關(guān)聯(lián)性、同一性的審查。這種舉證責(zé)任的分配方式,既可以規(guī)范流通環(huán)節(jié)的市場(chǎng)秩序,也可以防止侵權(quán)產(chǎn)品銷售者與他人串通,以提供虛假合法取得證據(jù)的方式逃避賠償責(zé)任。
作為市場(chǎng)主體,要求銷售商對(duì)所從事的商業(yè)活動(dòng)具備一定的認(rèn)知能力、盡到合理注意義務(wù)是公平的。上述兩條件在“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中緊密相連,最終目的是對(duì)銷售商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wù)”進(jìn)行判定。例如,即使銷售商知道其銷售的產(chǎn)品品牌非常知名,但及時(shí)索取了生產(chǎn)商生產(chǎn)該商品的授權(quán)證據(jù),且保留了可信的購貨證據(jù),依然可以適用“合法來源”抗辯。
在本案中,兩被告作為箱包行業(yè)多年的從業(yè)者,不可能不知道業(yè)界知名度極高的美國旅安公司及廣泛使用在安全鎖上的“”商標(biāo)。在這種情形下,兩被告亦未能提供真實(shí)有效的購貨證據(jù),顯然不能免除其賠償責(zé)任。
三、結(jié)語
《商標(biāo)法》的立法目的是促使生產(chǎn)、經(jīng)營者保證商品和服務(wù)質(zhì)量,維護(hù)商標(biāo)信譽(yù),以保障消費(fèi)者和生產(chǎn)、經(jīng)營者的利益。這就要求對(duì)假冒產(chǎn)品必須堅(jiān)決打擊。由于侵權(quán)配件的生產(chǎn)、儲(chǔ)藏、轉(zhuǎn)移非常便捷,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進(jìn)行打擊的難度往往較大,在銷售環(huán)節(jié)維權(quán)又缺乏相關(guān)經(jīng)驗(yàn)。河北高院的判決彌補(bǔ)了這一缺失,為商標(biāo)權(quán)人在更多的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進(jìn)行維權(quán)提供了支持,有利于維護(hù)市場(chǎng)交易的穩(wěn)定和健康發(fā)展。
本網(wǎng)站轉(zhuǎn)載的所有的文章、圖片、音頻視頻文件等資料的版權(quán)歸版權(quán)所有人所有,本網(wǎng)站采用的非原創(chuàng)文章及圖片等內(nèi)容無法一一和版權(quán)者聯(lián)系,如果所選內(nèi)容的文章作者及編輯認(rèn)為其作品不宜上網(wǎng)供大家瀏覽,或不應(yīng)無償使用,請(qǐng)及時(shí)留言通知我們,以迅速采取適當(dāng)措施,如刪除或支付稿酬,避免給雙方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整體產(chǎn)品上帶有假冒配件,這樣侵權(quán)嗎?